
编者按:
近日,第二届“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以“渺小与苍莽”为主题,旨在挖掘关照现实、书写时代与个体,记录磅礴与幽微的优秀佳作。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七猫中文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上海作协担当指导单位,《收获》杂志担当文学指导,关注时代浮沉、家国命运、城市与乡村、女性叙事、真实罪案等众多题材,倡导以诚实的书写,展现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貌,理解自我与他者。
作品《花园与父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父子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通过花园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父亲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心路历程。选题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和人文关怀,不仅是难得的疾病叙事,也是幽微的精神探索,在当下的非虚构写作中具有特别的意义。
以下是作者黄旭东的发言内容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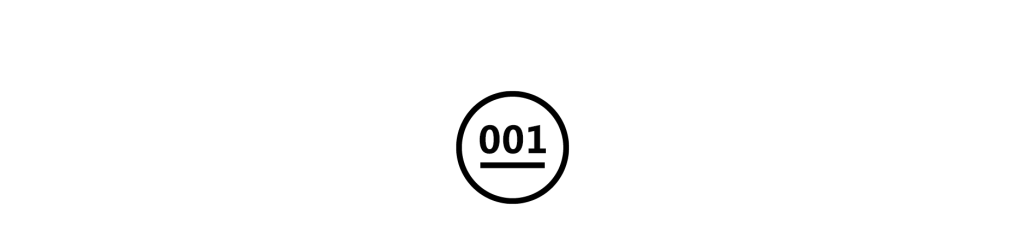
从私人叙事到文学建构
非虚构叙事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诗经》时代。那是一种原始的文学传统,叙事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他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同时也是在真实世界里大家熟识的那个人。人们相信某个故事是真的,不就是因为相信,眼前讲故事的这个人是真的吗?
这部作品写的是我们家庭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五年时间里,所经历的事情。主要有三件事:一是父子合力建造一个花园;二是为父亲即将离世做准备,着手选择墓地;三是为父亲治病。这三件事缠绕在一起,如果不写下来,这些深刻而复杂的体验就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什么也留不下。这便是我创作的初衷。
并且,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这部作品必须具备超越私人叙事的文学价值。因为如果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那么对于读者而言,它便没有阅读的意义与价值。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在构思和设计上下了些功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语言和修辞的要求。语言必须优美、精准,同时保持克制与节制,让文字本身拥有力量。
第二,对阅读效果的主动构建。在句子、段落乃至整体结构中,营造内在的张力与戏剧性,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期待。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作品搭建一个宏观的框架和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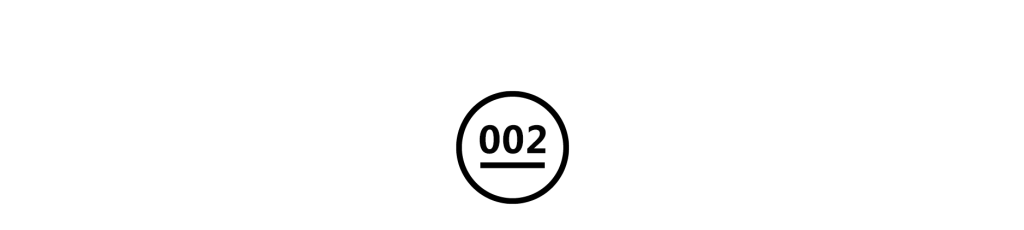
三条交织的叙事线索
在这个框架中,我梳理出了三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它们相互缠绕,共同构成了作品的骨架。
第一条主线,建筑活动和一个即将消亡的生命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建造花园,还是修建坟墓,都是人类从事的建筑活动,其本质追求的是一种“永固性”——建筑物要牢固,花园里的树木要能经年累月地沐浴阳光。然而,这些建筑活动,却又是围绕着父亲这个即将消逝的生命展开的。医生判断父亲的时日无多,但我们种下的树,却要期盼多年后的繁茂;我们修建的坟墓,本身又是对生命延续的一个寄托。
第二条主线,是“父子”之间角色的反转。 在我小时候,父亲是我仰望和模仿的对象。但当他患病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从一个儿子,变成了一个决策者,需要为他治病,为他安排后事,承担起全新的使命。这种角色的彻底反转,让我重新审视了与父亲的关系。
第三条主线,是“信与不信”的内心矛盾。 我们身处一个被称为“礼仪之邦”的文化中,对于疾病、丧葬,都有一套传统的习俗和礼仪。但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我,内心对这些仪式常常是怀疑的。然而,当真正面对死亡和疾病时,我又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甚至会不自觉地期待从这些仪式中得到依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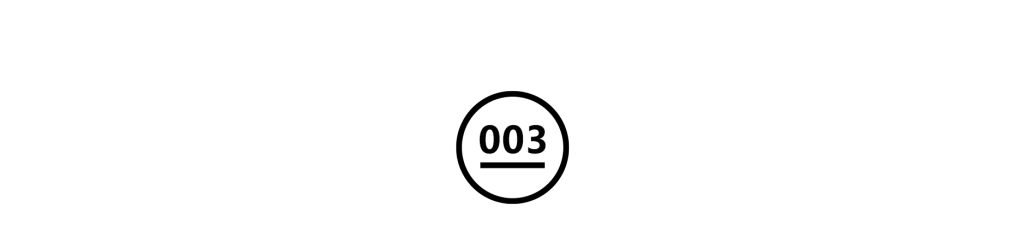
在废墟中飞翔
这三条线贯穿了整个作品的全过程。总体来说,还是归到了一个主题上:当你身处废墟,如何去构建新的东西,或者说当你面临像深渊一样的困境时,依然想要有一种飞翔的感觉,去寻找希望。
父亲正是在这样一个为自己建造坟墓的过程中,寻找一种价值感,一种意义感。就像农村的传统说法,人们相信墓地的方位和风水能给后代带来福祉,这种“相信”本身,就是父亲的一种希望。而我作为儿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同寻找着希望。
再谈一下题目。最初这个作品叫《如父如子》。后来有朋友说起花园这个意象,评委点评时也提到了花园这个意象。在这个作品中,花园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按照福柯的说法,“花园”是个异托邦,“疾病”是个异托邦,“坟墓”也是个异托邦。后来我把题目改成了《花园与父亲》,很多看似相反的事物,在同一个空间中共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作品也可以被看作是个异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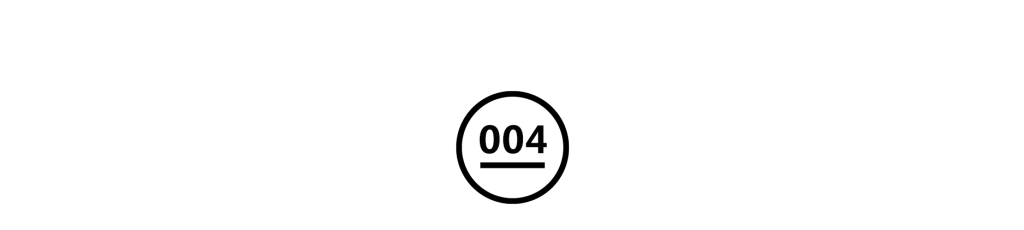
有那么一种非虚构写作
父亲生病不久,我就想着写点什么。它带给我的感受深刻而复杂,搜索自己有限的阅读史,发现那些既有的别人的文字,并不能触碰到我的痛痒。没人能替你说话,更没有这样一架机器,能自动扫描、读写你的内心。这事得自己来。
创作《花园与父亲》的过程,就是孜孜以求那些属于我自己的词汇和句子的过程。写着写着,我发现这是一个关于信与不信的故事,一对父子被疾病挟持,一边祛魅,一边赋魅,即使面对死亡,也要努力希望和意义——故事本来没有现成的版本,这个主题是我在写的过程中,逐渐体会、辨认出来并赋予它的。
我没有先入为主地去写父爱如山、父慈子孝之类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避免了类似卡夫卡笔下那个饥饿艺术家的悲剧。要真实地呈现饥饿,最好的办法不就是让自己真实地饿着吗?这位饥饿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也很努力。但其实并非如此。世上本没有饥饿这个词,人只是在真正的饥饿中发现了它;而不是相反,让它先找到你,主宰你的命运。
我愿意相信,非虚构叙事代表了这样一种写作路数,它为那个古老而朴素的文学使命而生,即人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境况。它一定不是AI写作,不是流水线作业,不是目前大多数意义上的写作。它是思考人如何成为更好的人这个意义上的写作。它是一种信条。
(编辑:吴筱慧;文字整理:苏怡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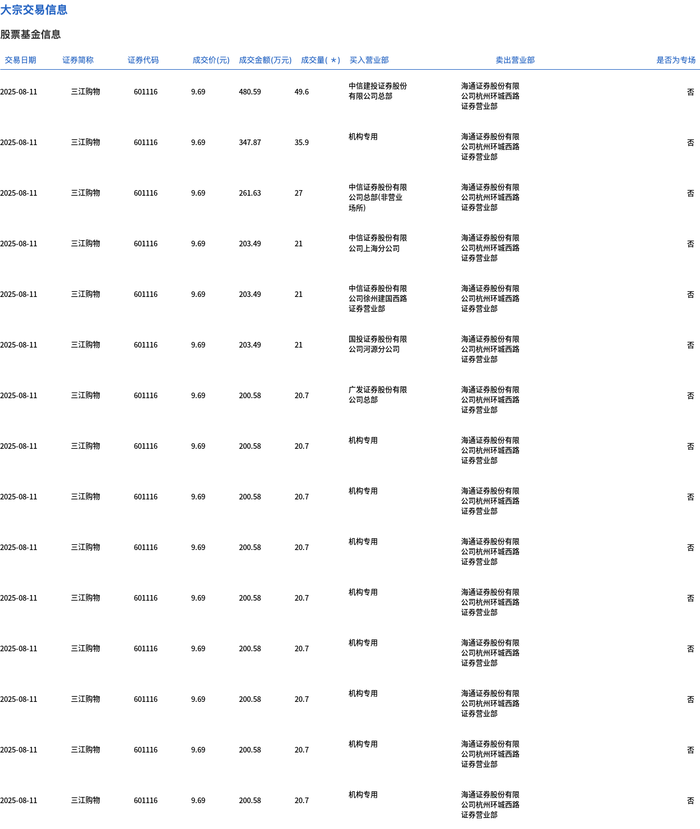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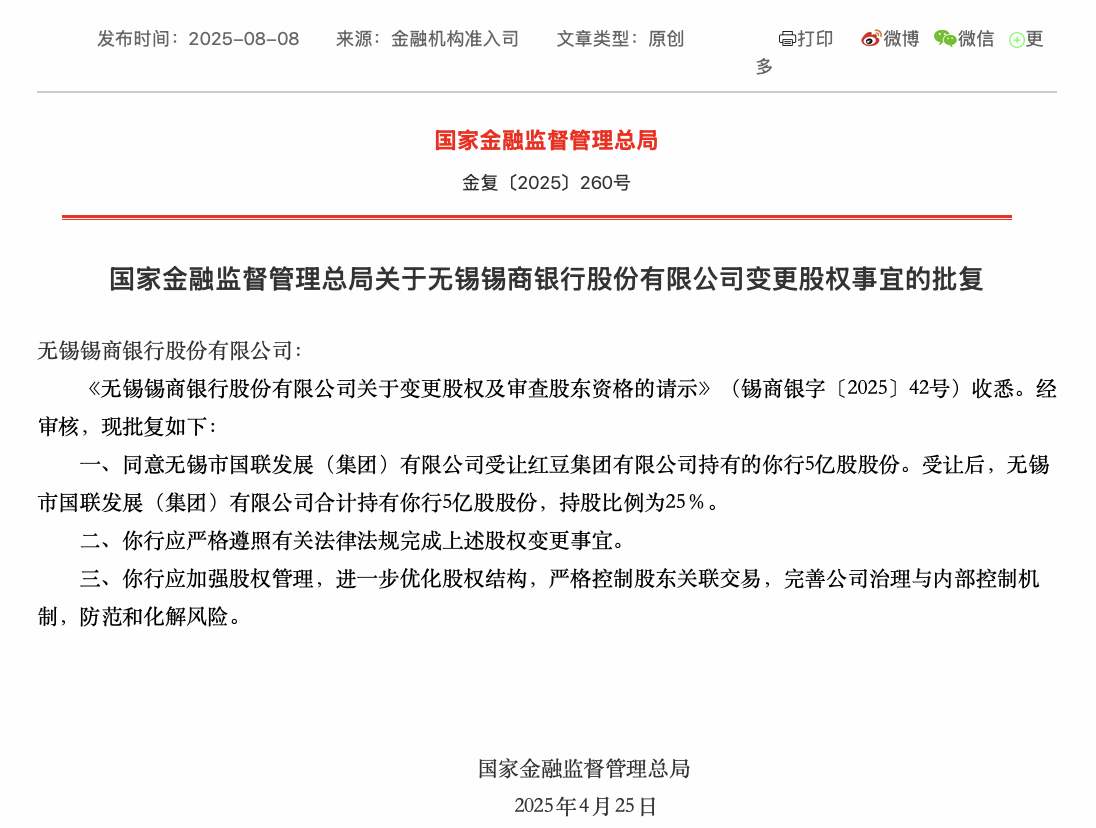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