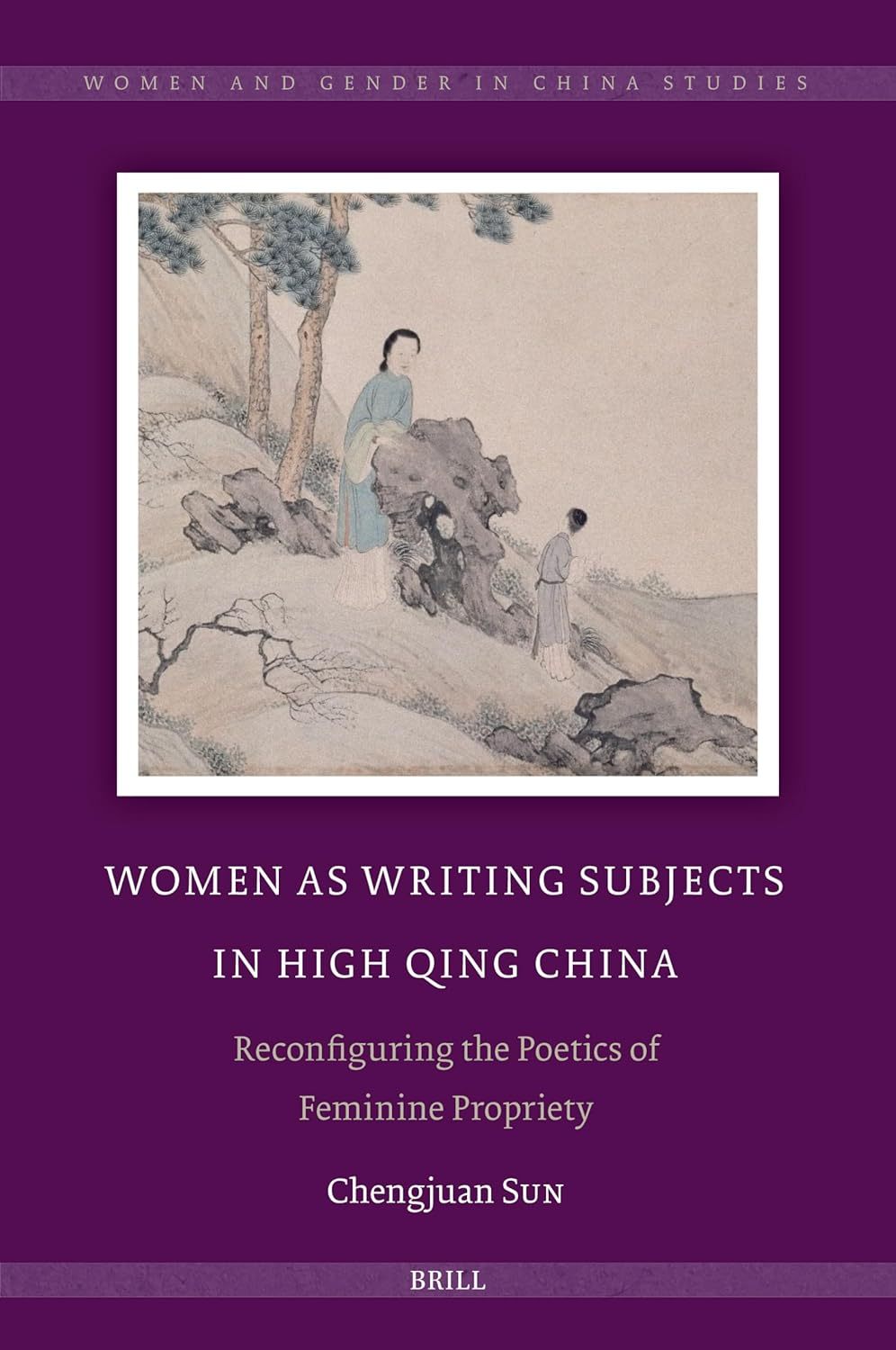
Chengjuan Sun, Women As Writing Subjects in High Qing China: Reconfiguring the Poetics of Feminine Propriety ,Brill, 2024
明清女性文学的文学价值
明清时期的女性写了大量的诗词。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些作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研究的时候,学者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研究女性诗词到底是社会史、文化史课题,还是文学课题?如果是前者,大家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把女作家的作品作为材料考察女性的家庭和社会经验,文化活动和社交网络,女性与法律、宗教的关系,母子关系等问题,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如果是把女性诗词作为文学来研究,就存在不少争议。早在清末民初,维新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就一方面肯定古代女诗人的存在,另一方面质疑女作家诗词的价值,比如梁启超、胡适都表达过女性诗词题材狭窄,大多写闺中生活与个人情感,因此文学价值不高的意见。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也还相当普遍。
但实际上,近二十年来的北美明清女性文学研究告诉我们,女性诗词远比我们以前知道的丰富多样、有创造力。李惠仪(Wai-yeeLi)、钱南秀的研究表明,明清女性诗词的题材并不狭窄,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写闺中生活;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易代之际,女作家更多写政治、写国难、写英雄气概,表达自己的政见、史识和豪情壮志。方秀洁(Grace Fong)、李小荣、杨海红的研究则说明,以闺阁日常为题材的女作家,在写作手法上也有诸多突破和发明,用以表达不同于男性文人的女性经验。到今天,这些作品是否值得作为文学来研究应该已经不是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去阅读具体的作品,在大量的细读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明清女性诗词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诗学思想方面的特点。这样的研究需要我们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女作家如何因为性别身份的不同而对文学传统进行改造?具体来说,女作家如何在男性建立的文学传统中书写自我,在男性主导的文化里表达主体性?女性写作发展出哪些独特的主题和文学表现手法?女作家怎样改写文学传统来表达她们自己关心的议题?
孙承娟2024年在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的英文专著,Women as Writing Subjects in High Qing China: Reconfiguring the Poetics of Feminine Propriety,这里译为《清中叶作为写作主体的女性:重构闺仪诗学》,就探讨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本书最有启发的地方是把明清女性文学当作文学来认真研究,以性别视角为基础,从具体作品出发分析女性文学与文学传统、女性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讨论女作家如何在男作家确立的诗歌传统中探索她们自己的诗歌语言。
“闺仪诗学”:闺秀诗人写作的策略和限度
这本书聚焦清中叶女作家的创作活动。清中叶指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时期常被称为中国古代女性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在明末清初)。此时的女作家主要是闺秀,也就是士绅阶层的闺中女性。作者在导论中提出,闺秀诗人的写作与文学传统、女性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清中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引起了很多关于女诗人应该写什么、怎么写的争论。作者认为,这些争论表现出人们对写女性的诗歌传统、对女性写诗的双重偏见。写女性的诗从宫体、香奁和词的传统中发展而来,这些作品一般被认为过于雕琢,缺乏实质内容,而这些负面评价又影响了对女性所写诗词的评价。清中叶的主流意见是,女诗人多写“绮罗香泽”,写得再好也不是最好的诗。面对这种批评,有些女诗人主张女性不要只写闺阁之事,而应该学习诗歌传统中的经典之作,比如杜甫那种“苍老高古”的丈夫气诗歌。但也有女诗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丈夫气诗歌写的是行旅、仕宦等男性经验,女性很难以此表达自己的心声。她们借用袁枚的“性灵说”肯定表现女性经验的价值。“性灵说”强调对生活体验的洞察,主张只要有天赋,谁都可以成为诗人。依照这个理论,女诗人不必模仿经典诗作,“何必论唐宋,诗原写性灵”,写自己的经验就好。
那么,闺秀诗人写了什么样的女性经验?书中提出,清中叶闺秀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关注性别规范和社会礼仪(gender and social propriety),在诗中认同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和女性美德,比如孝女、贤妻和贞妇。我们知道,清中叶正是满清政府为建立异族统治的合法性而倡导、推进儒家道德的高峰期,社会对寡妇再嫁、妇女失节等行为的批评越来越严苛。在这个社会背景下,闺秀诗人在写作中褒扬女性角色和女性美德,是不是被妇德的制度和教化规训了的结果?
孙承娟认为并非如此。她提出,清政府倡导的女性美德与闺秀写作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对妇德的要求使闺秀诗人在写作中进行“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不去写不符合社会礼仪和性别规范的作品。这无疑限制了题材的选择,比如她们一般避免直接写情欲,或者缠足、怀孕、生产这样的身体经验,不写钱,也较少表现愤怒、嫉妒和对抗的情绪。但另一方面,闺秀诗人也利用道德话语“自我赋能”(self-empowerment),表现为在妇德旗帜的庇护下追求自己的目标。比如,这一时期的女性诗集经常强调编纂目的是奉扬贞德,但集中收录的不少作品与贞德无关,这说明对妇德的肯定成为女性自我实现的修辞策略,或者说是一种道德包装,被用来提升女性文学的价值。在创作中,有些女作家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她们在诗中写自己是贤惠的妻子、贞洁的寡妇,是只写女性该写的文类和题材的作家,但同时也写那些不在妇德范围内、甚至与妇德相冲突的经验,比如向丈夫提出不符合他的利益的要求,追求名望和声誉,探索自我的精神世界,在文学和学术领域取得成就,等等。
这样的女性经验表达在明清以前的诗歌传统中是比较少的。诗歌传统中写女性的作品,比如宫体诗、香奁体和词,主要由男性文人创作,表现的是男性的关怀和兴趣,其中写到的女子往往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对她们的描写经常是感官化、情色化的,尤其关注她们的容貌才艺,以及相思、激情和闺怨等男女之情。但闺秀诗人的身份是女儿、妻子、寡妇和母亲,欲望话语和她们的身份、她们想要表现的经验不完全符合,所以她们需要对诗歌传统进行改写,探索表达处于自己阶层和位置上的女性经验的诗歌语言。对这样的诗学探索,孙承娟发明了poetics of feminine propriety这个词来概括。Propriety指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的社会礼仪、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书中用poetics of feminine propriety指闺秀诗人的作品具有符合性别规范、认同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和女性美德的诗学特征。这里译为“闺仪诗学”。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三位清中叶女诗人作品的分析和解读,这些个案研究展现了闺秀诗人如何在“自我审查”和“自我赋能”之间寻找平衡,如何改写诗歌传统进行自我表达。
三位女作家的自我表达
第一个个案是席佩兰,著有《长真阁集》八卷。她在世时就有诗名,与丈夫孙原湘是互相欣赏、互为知音的伴侣夫妻。孙承娟指出,席佩兰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夫妻之爱与列女传记中贤妻劝诫的传统进行创造性融合,在诗中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忠诚于丈夫的理想妻子,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给丈夫建议、劝诫和安慰,相伴相随,共同经历人生的喜悦和挑战。书中通过对比席佩兰和丈夫孙原湘写夫妻之情的不同方式,来说明席佩兰出于妻子身份的考虑和需要而对诗歌传统进行改写的情况。这里举一个例子。孙原湘把诗歌传统中的情欲表达直接拿过来写夫妻之情,比如他写的《春夜同道华》其三(小东风起玉鈎敲,却下重帘护燕巢。私语碧纱窗底月,为侬移上杏花梢),第三句源于《长恨歌》中的“夜半无人私语时”,表现他和席佩兰之间的情爱。第二句的“燕巢”指卧室,有帘子遮挡看不到里面,只听见风吹动帘钩的声音,也暗示亲密关系。相对比,席佩兰写夫妻之情就没有采用情欲表达,而是引入贤妻劝诫的道德话语,借用道德的话语向丈夫提出不要有闲情的要求。她在《以指甲赠外》(掺掺指爪脆珊瑚,金剪修圆露雪肤。付与檀奴收拾好,不须背痒倩麻姑)这首诗中,让丈夫带上自己的指甲,叮嘱他后背痒了不要去找麻姑抓背。席佩兰没有像她丈夫那样去写夫妻情爱,也是因为她要强调夫妇之间的感情高于情欲。她把男女之间的感情分为“闲情”和“至情”两种,前者指夫妻以外的男女之情,后者指夫妻之间的感情。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情欲表达是用来写“闲情”的,因此写“至情”就要与这个诗歌传统拉开距离。席佩兰在《情箴》一诗中对比了这两种感情,说夫妻以外的男女之情虽然迷人,但好像花光云影一样短暂,“闲情易抛却”,只有夫妻之间的感情才深刻长久,“至情金石坚”。
书中讨论的第二位女诗人是骆绮兰,著有《听秋轩诗集》。她三十三岁守寡后参与诗词书画雅集,当时很多名士为她的画题诗,或者为她的诗作画、唱和、写序跋和题赞。孙承娟用三章篇幅分析骆绮兰如何在诗中戏仿和改造描写女性的诗歌传统,把自己的寡居生活表现为智力和精神上的自主自足。从骆绮兰对诗歌传统的改写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作为男性文人欲望对象的女性和作为写作主体的女性有多么不同。书中分析的一个有趣例子是骆绮兰对香奁体诗歌的改写。骆绮兰不写香奁诗中反复出现的被情色化的女性形象,而是把视线转向男性的欲望凝视所看不到的闺房物品,比如做女红用的针线。即便是写钗钏、耳环、鞋子这些香奁诗常写的物件,她也尽量淡化其情色意味,而是强调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比如同样是写女子的鞋,香奁体鼻祖韩偓笔下的鞋是情色的,用来把玩的,“方寸肤圆光致致,白罗绣屟红托里”;而骆绮兰笔下的鞋是用来走路的,“行到花荫深径里,苍苔滑处自支持”,鞋子在湿滑的地上帮助女子保持平衡、站得稳,也象征着女子的独立自主。
书中分析的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骆绮兰对李商隐《燕台诗》的模仿和改造。虽然骆绮兰在诗歌语言、结构和风格等方面模仿了《燕台诗》,但不同于李商隐写少女的迷乱激情,骆绮兰写幸福的妻子和忠贞的寡妇。对独守闺房这个主题,两位诗人也有截然不同的视点。李商隐写恋人缺席时女性的绝望,如“芳根中断香心死”、“一寸相思一寸灰”,这是闺怨诗传统对独处女子的惯常表现。骆绮兰也写女性剩了一个人,但表现她的坚韧,她应对孤独时的镇定自若:“一寸芳心铸成铁”、“女贞青玉凌霜雪”。孙承娟还指出骆绮兰用孤鹤比喻自己的寓意。因为早寡、没有子女(后来她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好像离群的孤鹤一样悲伤;但同时,寡居生活提供的闲暇使她可以读书写作,可以享受“棋局茶烟”的愉悦,又好像孤鹤一般“逍遥”。孤鹤的意象突破了闺怨诗传统中女子因失去伴侣而孤独绝望的刻板形象。骆绮兰告诉我们,寡妇也可以有精神自由,有自我实现,可以有轻盈的人生:“此身自喜轻如鹤,佳处飞过偶一鸣”。
孙承娟讨论的第三位女诗人是汪端,她是席佩兰、骆绮兰下一代女作家中非常博学高产的一位。汪端最突出的身份是历史学者。她写的元明之际张士诚在江南建立张吴政权的《元明逸史》,是清代唯一由女性撰写的历史著作。不过这部史书没有流传下来,因为汪端将其焚毁,然后把她对这段历史的见解写进了组诗《元遗臣》和《张吴诸臣诗》中。孙承娟认为,汪端的这一举动表现出她与性别秩序的博弈。由于女性对国家治理和政治的兴趣被认为是违反了性别秩序,著述历史被认为不是女人该做的事,所以汪端焚毁了《元明逸史》。而相比史书,诗歌早已成为女性自我表达的合适载体,于是汪端选择了这个能被接受的渠道来发表自己的历史观点。最有意思的是,汪端想要在诗歌中传达的历史分析与评论,在咏史诗、怀古诗这些既有的历史题材诗歌传统中没有涵盖,所以需要发明新的诗歌语言。书中详细讨论了汪端为表达历史观点而发明的诗歌语言,比如她借用《春秋》褒贬功过的原则,采用并置和对比行为相近或相反的历史人物的手法,在诗中“激扬忠孝,表彰贞烈”。她还用长篇诗序来容纳历史分析和研究,包括讲述历史人物的事迹,比对互相矛盾的材料并提出自己的判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汪端在历史写作中对文体的选择,她焚毁史著、改写历史题材诗歌传统的做法,正是自我审查与自我赋能的结合。
“女性诗学”的可能
写作中自我审查与自我赋能并存的情况,在清代闺秀作家中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读古代女作家作品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寻找质疑或逾越父权社会中性别角色的直白表达。但孙承娟认为,闺秀诗人志不在此,这样的研究难以展开。很多时候,闺秀作家既认同已有的性别角色和女性美德,用社会规范要求自己,也借用道德话语表达自己的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她们实现主体性的曲折方式。作者提出,那种认为履行传统性别角色就是保守、质疑就是进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即便是对性别不平等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吴藻,也有履行孝女这个传统性别角色的一面。对社会规范和性别角色,闺秀诗人不是简单地服从或反抗,而是通过与规范博弈来发出自己的诗歌声音。博弈不只是挑战规范,也包括通过弘扬规范来追求自我实现。因此,闺秀诗人的作品经常既贞顺守礼,也以各种方式夹带私货,发出规范以外的声音。书中强调,“闺仪诗学”的生命力正来自这种既重申、又重构女性规范的张力;因此研究闺秀诗人的作品,重点不是去追问女性写作究竟是顺从还是抵抗父权秩序,而是考察女作家如何借用文学资源和思想资源、如何通过改写文学传统来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赋能。我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书中讨论的三位女作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席佩兰和骆绮兰学诗画于文坛和书画界大家袁枚、王文治,拓展了她们社会交游网络;汪端出生于书香仕宦世家,对她影响很深的姨母梁德绳是当时著名的闺秀作家,公公陈文述是著名诗人。她们的位置和处境可能使她们有更多自我表达的空间。
从孙承娟的“闺仪诗学”论述想到,或许“女性诗学”可以作为考察明清女性诗词的一种角度。这里的“女性诗学”可以界定为由于男性建立的文学范式和惯例不能满足女性自我表达的需要,女诗人对文学传统进行突破和改造,探索自己的诗歌语言。“女性诗学”是复数的,处于不同时代、地域和处境中的女作家可能形成不同的诗学语言。例如,清中叶作为女儿、妻子、寡妇和母亲的闺秀作家有符合社会礼仪、性别规范的“闺仪诗学”,但同一时期的妾就不那么关注礼仪规范,侧室在家庭中较低的身份使她们可以更自由地写情欲、写身体。再比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经历战乱国难的女性,比和平时期的女作家更多写家国大事和英雄气概,因为政治的动荡促发女性在诗文中突破传统的性别角色。又比如,清朝北京的满族女作家和江南的闺秀作家又因为阶级、地域和民族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诗歌题材和写作手法。“女性诗学”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女作家因性别身份和经验的不同而对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改写的现象和成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思考明清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